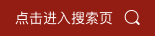一门课程与几个瞬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23级硕士生 翁宗弛
做农村研究的学生,无论从哪个方面做起,兜兜转转都会遇到《华北》、《长江》两部著作,随后由此而始,结识黄宗智老师。我同样如此。今年5月份,实践历史与社科研究公众号发布了2025届研修班的招募通知,我仔细读过后,就把页面关掉了:刚刚接触农村研究一年多,我对自己的学识和能力都不够自信。没几天,我的导师黄家亮老师把通知转发给我,鼓励我试一试。我功利地想,那就试试,正好借机会重读一遍《华北》,看看能不能对我毕业论文所做的乡村集市研究有些启发,至于是否录取就听上天安排。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参与其中才发现,八周的课程实际上十分紧凑,其中我还有两周在暑期调研,左支右绌。两个月的时间就这样一本书一本书地、紧张地过完了。研修班的惯例是结束后要提交一份感想,借此机会我想再次梳理一下,课程结束后,不会像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繁杂知识一样慢慢从我脑子里淡去的几个瞬间,也与大家分享。这几个瞬间,于我而言是顿悟,用黄宗智老师的话讲,就是像钓鱼一样,经历了漫长等待后鱼上钩的狂喜。我很清楚,这样的瞬间一生中不会有太多次,且往往要付出许多代价——我将受益终生。
首先是“求真”。在讲恰亚诺夫那堂课上,高原老师很激动地说到恰亚诺夫、黄宗智都是对真理有强烈追求的人,这种精神是很伟大的。如高原老师所说,黄宗智老师的研究是带着我们触摸真实的世界,而真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搞清楚的。这对我而言不亚于地震:在我自己为数不多的研究经历中,我并没有自觉、自明地“求真”,这不是说学术造假,而是意味着我并没有那种探究真实的毅力和强烈的好奇心(但这样做出研究与学术造假何异呢?)。正因此,我要么陷入对研究感到厌倦,认为“事情的全貌就是这样了”的虚无,要么陷入“事情本身如此复杂我怎么可能搞清楚”的不可知论。从这两个方面说,对“求真”强调与明确不仅是精神层面的激励,也是方法论层面的教育。于我而言,明白这一点,比所有的知识都要珍贵。
意识到这种求真的精神,实践社会科学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套范式向我们展示了求真的途径。实践社会科学首先意味着我们应当转向实践,这种实践转向让我们避免了各式各样的二元对立,也即各式各样的对世界的非真实构造。但是不同于(超越于)布迪厄的实践概念的是,也让我们更接近真实的是,黄宗智老师对“说、做、合”这一框架的阐明:表达的是一回事,实践的是另一回事,二者合起来又是另一回事,这在理论上扩展了“实践”的内涵,也提供了一套操作框架。这里对“真实”的强调,可能会让人误解这又陷入了实证主义那种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真实的、带着自然科学色彩的错误想法。实际上,实践社会科学从不声称能够建立一种普适的理论,而是往返于理论和实践之间,永不停息。面对无限多变、多元并存的实践,研究者在有限的经验上形成有限的理论,再不断地去检验,这不是退缩,是求真精神的另一面而已。
由于学科基础薄弱,我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论思想,像一个刚过门的媳妇一样,做研究瞻前顾后,我不清楚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我十分渴望寻找到一个自己信服的、系统的范式。研修班上对实践社会科学系统的介绍对于刚做研究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本宝典。这是我第二个幸福的时刻。
第三个收获则是宽阔的理论视野和系统的阅读方法,实际上,这是我申请的初衷(那时我不会想到我的收获远超于此)。当时,中间四周的理论阅读我多少有些云里雾里,用一周时间阅读一个理论流派的代表作常常是还没有很全面的掌握,就进入另一个甚至理论旨趣完全相反的流派当中。但准备第八周课程阅读材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样安排的妙处:黄老师实际上对形式主义、实质主义、后现代理论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马克思主义)有十分全面的评析,而我们只有先明白不是什么,才能更清楚的知道实践社会科学是什么。尽管课程意不在让我们全面掌握这些理论,但是四周的理论阅读还是给我初步建立起来一个宽阔的理论视野,更深入的了解应当在课下。至于阅读的方法,实际上课程招募时已经详细介绍过。额外的收获是各位老师在课上提到的:理论著作的阅读应当明确其对手,经验著作的阅读则需要对比吸收——这让我少走不知多少弯路。
八节课,24小时,我的收获远超这里所记录的。感谢赵珊老师、高原老师、赵刘洋老师、蒋正阳老师一路的支持和付出,你们是我的榜样。感谢研修班一同学习的同学们,你们的分享给我许多启发,鞭策我朝向优秀的方向前进。
衷心感谢黄宗智老师,感谢老师对青年学生的传道授业、关怀和鼓励,这对一个学生来讲是极为幸运而又幸福的事情。最后一节课上,黄老师高兴地向我们讲了许久,由于课程时间恰好是美国的凌晨,老师身后的百叶窗从浸于夜色到透出明亮的晨光,我想这一幕很有意义,我也同样被照亮了。
2025年10月9日
于人大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