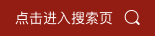实践与理论之间求索
——2025年“实践社会科学:历史与理论”研修班感悟
张翼 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生
研修班结束已有数周,提笔撰写感悟,却不知从何写起,该如何描绘这一学术共同体呢,又该如何呈现这八周的精神洗礼与思想共鸣呢?随着时光流转,回想研修班的学习细节,其中多数或许已在脑海中逐渐模糊,但一些场景依然清晰,令我感动:第一堂课伊始,黄宗智老师举起双拳,一边代表理论,一边代表实践,呼吁我们的学术研究必须“双手并用”,强调连接理论与经验是学术研究的起点。这种实践与理论的持续互动,一直延伸到最后一堂课,黄老师再次以现实生活举例:“我们认识朋友也是这样啊,既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也不能只看他做了什么,而是要在说和做的主客观二元互动中认识”。是故,我选择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作为我撰写感想的起点与贯穿全篇的线索,与诸位分享研修班带给我的几个关键转变。
一、从“陷入自我思考”到“把握作者观点”
无论是阅读经验性专著还是理论性专著,黄宗智老师都反复强调“必须精准掌握其中心论点,并用自己的话概括出来”的读书方法,对我而言,这是一场较为彻底的阅读革命。过去阅读任何学术专著,常常陷入“有感而发”式的读后感写作,或是被理论的宏大叙事所吸引,最后完成的读书笔记往往完全成为自己思想的主观表达,却忽略了作者在实践层面真正期望表达的核心论点与经验支撑,如此的读书笔记只能算是个人想法,而非一般性知识,正如四位助教老师所言:“也许过段时间回看自己的笔记,只能是与当时的自己对话,而不是同作者交流,更谈不上理论对话与使用。”
鉴于此,研修班的前几周,我就被要求用一段话甚至一句话概括学术专著的核心观点,并梳理其经验证据与次级论点之间的逻辑链条。这种训练颇具难度,黄老师读者友好型的写作方法,使我曾一度以为自己完全把握了《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的全部内容,甚至沾沾自喜地对原书逻辑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主观划分,然而,在课堂分享中我被指出“未能抓住黄老师法律史研究中‘表达与实践二者既抱合又背离的一面’”。那一刻,我便意识到自己过去对经典著作的阅读仍停留在“自我判断”而非“知识还原与思想对话”。正如黄老师所说:读者没有掌握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对作者最大的不尊重。作为阅读者,必须重新审视自己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之后每次笔记撰写中,我都将精确把握观点作为阅读的第一要务,时刻向自己提问:作者在此想要表达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写?力求以原原本本的观点还原,替代脑海中隐含的主观预设。
二、从“理论先行”到“实践出发”
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是一场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源于对长期以来西方形式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现实时无力与脱节的回应与反击。在我关注的中国政府组织研究领域中,便有充分的实践对此予以证明,周黎安老师在与黄老师的对话中将其总结为:“集权架构下‘碎片化’权威与领导小组集中统一和‘共识型’决策相对照……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协商式民主和政企合作。”上述众多西方理论隐含前提与预设造成的“中国悖论”,曾让我陷入长时段的研究困境,这种困境促使人不得不回归思考“如何认识中国”这一基础性命题,而黄老师贯穿于研修班课程中的“从实践出发”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恰是这种悖论与矛盾的超越性解决路径。
“不要从理论出发去裁剪实践,而要从实践出发去检视理论”。在阅读黄宗智老师“正义体系三部曲”的三周课程中,我尤其被“第三领域”“集权的简约治理”以及“革命时期的法庭调解”等概念提出过程所震撼。这些概念从紧贴真实世界的经验出发,源于对大量清代司法档案的细致梳理与实践逻辑的提炼,而后凭借“合理推断”来发现特定经验现象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把抽象概念延伸、推广并形成有限适用性的理论,进而避免脱离真实世界的高度简单化、片面化和理想化的设定,最终,再将理论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并如此不断往复于经验与理论之间,最终达到准确把握真实世界并提出深刻的理论洞见的目的。由此可见,实践社科的研究方法不固定追求高度的理论化或丰富的经验证据二者任何一方,而是尝试超越抽象化与经验堆砌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进而塑造连接理论与经验的学术研究,这不是一套明晰准确的方法论,不过也许正因其动态变易的研究进路,才能“拉着读者的手”去触及、还原真实世界——因为真实世界本来便不某一是固定的理论范式。
三、从“学术训练”到“情感认同”
“理论家可能就是吹牛家”,黄老师在首堂课便提出此观点,这句话初听令人惊愕,细思却极具深意。黄宗智老师并非否定理论,而是反对脱离实践的理论空转,反对为理论而理论的学术游戏训练,他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唯有在解释实践中才能体现,鼓励我们采取多元理论的包容态度。这意味着不把任一理论当作给定、全面的真理,而是对各理论流派采取选择性地使用、改组或推进的态度,取其有用的部分以认识、理解、表达自己深入经验研究的发现,将理论作为经验认识和理解的有用工具而非先验的假设,进而搭配使用“一竿子插到底”的经验证据,直面真实世界的问题,这种对真实世界的还原与分析紧紧依赖一种研究的“真实感”。
那么什么是真实感呢?就此问题,赵珊老师、瑞华师姐和泽玮师兄曾给予我极为有益的建议与答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我将他们的答案总结为基于个人经历的情感认同,黄老师的真实感源于他对中国人民广博且深刻的学术关怀,而我的真实感则来自我是一个天津宝坻(原河北省宝坻县)的学生,我的家乡正是黄老师清代民事案件的收集地与华北地区小农经济调研的覆盖地,黄老师关于华北小农经济与清代民事法律的研究,与我成长中的许多记忆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我的祖辈生活的村庄俗称“大洼”地区,其名源于该地区长年面临严重水旱灾害的现实情形,这正与黄老师《华北》一书对华北村庄自然条件的描述相符,也称为农业“内卷化”的形成条件之一;我的祖辈同样不愿轻易打官司,认为“对簿公堂”是在村庄中破坏良好关系、不留颜面之事,这种“息讼”心态正是黄老师笔下“简约治理”的社会基础。这种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呼应,让我感受到“实践社会科学”不仅是方法论,更是一种扎根中国大地、关怀人民生活的学术情怀,我想,这种情感认同也许正是一种“真实感”。
四、结语:缘起实践,归于真实,服务人民
回想本科毕业之际,我怀着对黄宗智先生学术思想的崇敬与对“实践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浓厚兴趣,作为一名即将进入政治学领域深造的学生,走进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学术共同体。而今回首,这段经历不仅重塑了我的阅读方式与研究视野,更让我对“何为真学问”“为何做研究”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我将这种体认归纳为:缘起实践,归于真实,服务人民,其中何为“缘起实践,归于真实”我已在前述论证中予以说明,最后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何为“服务人民”。
在我之前听过的绝大多数课堂讲授与学术讲座中,谈及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或是其判断标准是什么的时候,学者们给出的答案基本类似:好的学术研究应该受到自己老师的认可,应该受到国内学界的认可,应该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这样的答案固然是正确的,但似乎忽视了人民共和国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黄宗智老师在其学术生涯中所最重视、最关切的一点,即,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从华北的小农到当今的非正规经济,从清代民事纠纷到新时代的社区调解,黄老师身体力行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学者对中国普通人民的感情和认同,也使我在研究中不断反问自己:我的研究对认识中国有什么用,对中国的老百姓有什么用?我想,这也许是判断我学术研究水平高低的最核心标准。
最后,作为研修班年龄最小的学生,老师们与师兄师姐给予了我极大的扶持与帮助,研修班数周,切磋砥砺,受益匪浅,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感谢黄宗智老师以八旬高龄仍坚持凌晨四点为我们授课,愿您与白凯老师身体康健,思想常青,学术永茂。
感谢高原、赵刘洋、蒋正阳与赵珊四位助教老师的辛勤付出与智慧陪伴,祝老师们学术精进,桃李满园,生活静好。
感谢林泽玮、徐逸为、孙瑞华、邱昊龙、罗锴、毛润禾、武廷会、翁宗弛、李志鹏、匡俊锋、冉婷匀给予我的思维碰撞与真诚交流,愿各位师兄师姐前程似锦,学运昌隆,不负韶华。
谨撰此文,献给乙巳年盛夏“实践社会科学:历史与理论”研修班。
2025年10月3日于鼎新图书馆